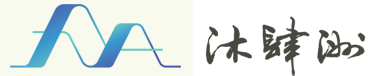爱上纪录片采访《园林》制作
作者:沐肆洲

一、制作《园林》的过程中,与金明哲导演之间的博弈故事。
“爱上纪录片”让我讲讲在纪录片《园林》制作中,我和金明哲之间博弈的故事。
博弈,其实谈不上。作为纪录片的音乐设计者,或者说声音创作者,我需要做的,并非绞尽脑汁跟导演较劲,以坚持自己貌似坚定和成熟的艺术观点与审美眼光。从业多年来,我自觉最大的收获便是可以接受多种审美,并能理解之、认同之、追求之、实现之。况且,我脑海中圣殿级的纪录片类型,我所能加分的部分,刨除声画关系之类基础理论外,能做的只是技术层面。目前我这么认为,影片是导演的经历,我应该为之调剂、与之游戏,辅之表达,而早已不会与之博弈甚至对立。而这一切,源于以前自己狂风暴雨般的不更事的主意。
分寸,不论是为人,还是做艺,都是难以企及的高端境界。
这篇文章里,我不会谈到任何关于声音制作技巧和纪录片声画关系等理论问题,有这方面诉求者请绕行。唯如久违老友相聚,沏茶聊天。
而第一时间闪在我脑子里的,还是几个有着明显记忆的节点。可能这些节点本身并不能说明说明问题,但连贯起来从远处看看,会酝酿出一种交往的方式,以及过程中飘来的人的味道。
缘起
2012年夏天,广安门外,路边海鲜摊。
金明哲攒的局,原定4-5人聚会,只到了金明哲跟我俩人。一桌海鲜(4-5人量),两盘凉菜,一瓶二锅头,数瓶啤酒。
恍然记得,他拿出IPHONE 4手机,里面是一位身着红蟒帅盔,背插锦缎靠旗的武旦美女在飘然自旋,还有金明哲因喝多而飘忽地无法稳持手机的胖手。
对于金明哲刚刚拍完的这些纪录片《京剧》的高速镜头,我深表赞叹,并且感觉的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与热情;但却说不出为什么好,好在哪里。我自幼学西方音乐,对于中国戏剧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形式美层面。
关于席间他给我谈到的他的下一部大作——《园林》的音乐声音制作工作,我未敢应承——当时我相当然地认为,这或许仅是一部带有浓郁中国风格的纪录片,顶多再讲到一些园林的来由和文化脉络之类。我对于不熟悉的音乐领域,心虚的很。
酒没浪费。从那至今,我没再敢跟金明哲喝过。临别,他把我揉进出租车。我四脚着地爬上楼道,勉强到家——那天好像是回到家了吧!好像是他结的账。
他若是伯乐,我却不敢做他的千里马。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太沉厚。思想和体型皆如此。
从07年跟金明哲结识以来,他一直是我最偏向的一种导演,因为他不管我。我做完片子之后,他极少改动,他说希望每个人对他的片子有不同角度和方式进行解构、解读,片子才有意思。但在做片子前,他都会给我讲很多与审美理念相关,但有不涉及片子内容的内容。比如做《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第11集《浪漫主义》之前他跟我聊的“暴力美学”。我至今都认为,这是最好的总导演和制作人员(包括摄影、解说等)交流的方式,这些“务虚”的东西,也是这些年来我做纪录片声音工作最大受用的部分。
半年后的三月,国家大剧院《美丽中国》音乐会现场结束,我心里激动地充满着纪录片音乐会带来的幻境。在呼啸的北风和长安街摇曳的橘黄色灯影中,我发消息给金明哲:“我想给做园林做音乐。”他回复:“好啊!一块儿弄呗!”
从宣传片开始
“我不想把宣传片音乐搞得太传统,太民族形式,但一定要有中国文化的美学核心,比如昆曲那么丝丝入扣的东西。你可以放开了弄,可以现代一些”。
“成,太好了”。
我的这句“太好了”,一是赞同他的观点,而是暗自窃喜:你叫我写纯民族的东西,我也写不出来。
我开始天天听昆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昆曲。几天下来,我完全记不住一句旋律,甚至连拍子都跟着打不出来。
在一段时间内强制性地听一种东西,即使背不过,但也会形成一个笼统的印象。一个礼拜之后,我只憋出了那四个音符,就是那个宣传片音乐中,大提琴演奏的那四个音。
人都是被强逼出来的。既然豁出去接了这个雷,就不能叫它炸在手里。但想端稳了,很吃力。有一个给你雷的人,而且他允许我按照自己最舒服的姿势端着,这就是金明哲。每个项目都是。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不免狭隘了。音乐的地域文化性,未必只是从乐器的选择表现出来。乐器只是元素,不论选择西乐还是民乐,它只是听众的潜意识中众多情感与心境来源于组成之一。你同样可以从没有听过的非洲土著音乐中听出他们目前是快乐,还是哀伤。正所谓音乐无国界。
况且,金明哲想说的园林,本来就没有这么狭隘。
从那四个音开始之后的半年里,与我合作多年的小兄弟孙沛,协同一起完整了园林的约30分钟的作曲。整体曲风温和细腻,貌似简单但颇为耗神,希望有变化却怕变得肤浅,欲求空灵却怕做成空洞。
音乐,不是用来叙事的。你单听音乐,我想说的事儿,你一个也听不出来。音乐只做两件事:用音乐作为催化剂,让你更舒服的看金明哲等导演的叙事;以及隐含着表达一点我对于导演们讲的故事的自己观点。说白了,有态度,别捣乱。
正片
所有艺术的产生都可分为两部分。创意部分、创作部分。当思想上达成了统一、心心相惜之后,有些基础性的工作,便可以开始了。在这段时间里,谈不到什么艺术,谈的是“别犯错误”,照规矩来。就好像为了创作维纳斯雕像,人们需要去山里刨出来大理石一样。这个过程是有点枯燥的。当然,作为真正的热爱,是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我目前还达不到。
在这个过程中,我跟剧组跑到了几个地方。苏州、河南云台山、台湾,采集了不少难得的素材。这些素材被大量使用在影片中。因此,这也是我参与过的同期声采集、使用、修补最多,也接近于自然本真的纪录片项目。作为纪录片录音师,不是声响的创作者,而是大自然声响的挑选工和搬运工。选好了,小心翼翼拿回来,仔细筛选、加工,放在影片中,送到观众客厅里。即使这样,就算我用了最好的麦克风与最科学的方法,加之观众用了最好的音响与听音环境播放,我也觉得它无法与我在当地所闻相比,也不如大自然的创造。你如果与我一样到了那里,所有人为的声音都是冗赘的,包括音乐。
再次特别感激金明哲、汪喆等导演对声音的重视。与你们出行听到的声音,是我在录音棚里一辈子也想不出来的。
这么大的工作量,我一个人自然是做不完的。沐肆洲的兄弟姐妹们在不尽繁杂声响方面的创作,为后续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大量同期录音无法实现的时候,他们将大家所看到的所有画面中、外可能会出现的声响全部一丝不苟的制作出来,包括每一声脚步、每一颗水滴,甚至是手沾在薄如蝉翼的纸张上面的声音——即使我在最后出于整体考虑拿掉了一些。
纪录片若想好看,关键在故事与叙事;细节的展示,不论是镜头还是声响,都是可以大大鲜活之的。
具体的创作没有什么戏剧冲突,无非是对于一些具体点的不同理解,金明哲与我有过一些争论。比如,关于8集《园林》是否需要风格统一的问题,我曾用手机打给他一篇几百字的微信去劝解与坚持。我固执的认为应该统一,以显示整体感;而他告诉我,园林风格不同,8集并非之表现一种园林的风格,也理应不尽相同,其实这也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当时显然说服了我。时至今日回想当初,我那种执着多么的幼稚。这也是金明哲通过园林给我上的终生难忘的需要“打通自己”的一课。
底线
与任何纪录片一样,在过程中,总会有一些让人不堪的困境。金明哲曾在极端无助的情况下给我说过一句话:“我几乎要放弃一个导演的底线”。
这说明他还是知道底线在哪里,并且有底线的。这已然是个高标准。
在后面的工作中,其中有一集,他针对好几个地方反复调整、修改,我看到修改意见后,在微信群里给他写了一句话:“看修改量我就知道,老金是个不会放弃底线的好导演!”
困难一定是有的。越是有追求,困难就越大。现在面临播出,那些苦哈哈的抱怨理应烟消云散,大家都等着喝开播酒的时候,这些事情姑且就不写了。倘若此些内容由我写出来,仅凭我亲历的众多纪录片项目,便很容易搞得过于血淋淋。也正是因为像金明哲等等无数有底线的纪录片人,在支撑着、擦拭着这个血淋淋。
结束了
2015年6月10日,20点33分,《园林》后期工作微信群。群名:曙光照在园林。
相信每个做过纪录片的人都无比懂得这个“曙光”的意思。
金明哲:@王同收工!辛苦!
我:就这么结束了?
金明哲:@王同你再干我没意见!
我:有点突然。可能是惯性没停下,园林里睡着没醒透。
张舒(第一集导演):续上旧梦做新梦
金天龙(制片):去如春梦了无痕
金明哲:遇上新人还旧梦
我一直对于金明哲的第二句话没看太懂。
三年的项目就如此结束,忽然觉得时间过得好快。这三年,其实也是我真正开始对纪录片、对纪录片的各个部分产生一些思考的三年。现在看来,很多创作观点都是与《园林》、与金明哲有很大关系的。
还是回到博弈上来吧,也作为上述文字的小总结。
博弈的前提是在一盘棋上。
博弈并非时刻冲突,而是伴随着随时向对方学习。
博弈的两个人都需要底线,要有秩序,要有规矩。尊重对方,尊重棋局,不能偷奸耍滑,不可拿起棋子掷向对方,不可半途而废。
博弈是个脑力活,靠蛮力不行,没脑子不行。
博弈中的每一步,都是“气”。金明哲说,气不要断,不要堵,气要顺。
博弈其实靠的是“势”。知进易,知退难。一部影片的各个工种亦是如此。
二、每个人都有一些情结,用心工作时,很容易触动到那些情结。
在制作《园林》的过程中,您的哪些情结被触动,可以讲讲您的那个情结故事吗?
《园林》给我的触动点很多。与其说“触动”,不如更进一步说“影响”。或者是给了我以后人生道路了一个方向。
年轻人比起成熟人,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是对一件事情的衡量标准是否足够多和平衡。在经历些了风浪后,所谓的心平气和不动声色,其实是看到了事情的多面性而不再惊呼。
《园林》便是这种风浪。把我拍打醒悟。
对于上林苑,对于桃花源、对于艮岳和拙政园,这些过去人创造的美景空间,我们通常以眼睛观之,以耳闻之;加上中学历史课本中的解释,我依然觉得过于肤浅和冷冰冰。殊不知每块城墙、每棵毛竹,每块太湖石的背后,有人的温度。金明哲让历史人物作为人——而不是历史标志物的一面出现在《园林》中的时候,换个角度,感其思、洞其愿的时候,对于我们当下的人生或许更有意义。
我猜想,看过的观众或许会有人说《园林》是“百无一用”之物,是避世之举。看似说玩花弄草逗鸟赏鱼,实则为缓冲社会现实与个体诉求之间的矛盾。不瞒你说,几年前,我也愤青的很。
正像是园林风格的变迁,社会的变迁也在遵循着自己的规律;正像园林中的故事在历史上的不断重演,人类社会或许从来就没有进步过,只不过在原地循环画圈圈。
作为个体的人,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大环境,而是自我个体的问题。说市侩,首先你要不市侩;说公平,首先你要够理智;说急功近利,首先你要安分守己;说物欲横流,首先你要无欲无求;说世态炎凉,首先你要观物如己——这也是你目前唯一能解决的。
在这个问题上点醒我的,三年来,《园林》功在首位。
对于物的关爱,《园林》中有大量的介绍。园林中的物,是人的基因中向往自然之物化,也是源于常人很难企及的对万物的悲悯之心。爱物,便是爱己;爱己,便会爱人。那种细致入微的镜头,让我有为它做音效的冲动,而且乐于长时间对着一个声音反复摆弄。比起文震亨来,作为一个做声音的匠人,追求极致的劲头,我还远未达标。这也是我需要解决的个体问题。
记得刚入行的时候,我还曾做过一件事:数一下一集纪录片中我做了多少个声音,用总制作费除以这个数字,便或可知我做每个声音的价值几何;通过我的制作周期可算出每分钟我的收入是多少。这种细算法在当今工业流水线社会堪称“管理心法”。但在这种量化的标准下,人的诉求究竟何在?
总还要有一些偏执的东西在规正着人最基准的需求,同时也随时有着合情合理的物欲左右着我们。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便是我这样的人一直把握不好的;甚至有一些人已经忘记了人最基本的满足与快乐来自何处。
《园林》触动到我的这个点,也正是当下社会人普遍存在的无奈的地方。万物有阴阳之分,人体有内外之别。当可a以静下来的时候,不如静默思考,享受内心丰满的世界——如果你内心足够丰满,四肢不动、耳目不染依然可以自娱自乐的话。
多年来,我活的太外了。不外谁给钱呀!不外怎么宣传营销呀!现在还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么?这是一个处处毛遂的时代呀!
外强必中干。
谢谢《园林》,谢谢金明哲,谢谢所有喜欢《园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