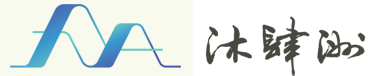央视剧评 |专访《文学的故乡》总导演张同道:探寻中国当代作家的精神花园
转自:央视纪录
央视剧评 |专访《文学的故乡》总导演张同道:探寻中国当代作家的精神花园
“一个作家写作,应该有自己的一块故土,建立属于自己的一个文学王国,可以一辈子只写这一个小地方,但这个小地方,在某种意义上应该代表国家。”
——莫言

一片故土滋养着一方心灵,作家因地缘不同形成各自独有的风骨,但看似游散的文学命题,因“故乡”的追寻而呈现出清晰的成长脉络。
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拍摄呈现了六位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阿来、迟子建、毕飞宇、刘震云、莫言,“与其说作家选择了土地,不如说土地选择了作家——高密东北乡选择了莫言,秦岭商州选择了贾平凹。”迟子建走在故乡的雪原,她说:“好像每一粒雪都在向我诉说……”
纪录片《文学的故乡》跟随作家走进了他们的故乡,也走近了他们的作品,更是同频体味了他们的精神家园。
这是中国电视人第一次以影像为载体寻找文学的发生与萌芽,作品播出以后,收获了一片震撼,导演张同道接受了“央视剧评”的专访,讲述了该片的缘起及形成。
文学的内容很广泛,
为何以“故乡”为核心?
“我们选择文学的故乡,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那就是纪录片需要表达,需要找到表现形式。”

“故乡,它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同时它又是作家创作的原点,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在故乡这样一个环境中形成生命最初的认知,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作家的气质,决定了一个作家的表达方式,甚至他创作的母题,故乡这样一个物理性的存在,使作家获得了一个创作的支点,从纪录片来讲,也获得了一个进入文学的通道,如果去拍现代派文学,它是一种精神性的、心理性的东西,在视觉呈现的手段上就少了很多。”
为何甄选这六位作家?
“首先,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它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景,选择这六个作家就是代表了六种不同的地理风貌。从最北冰天雪地的黑龙江,往南到高粱满地的山东高密,再到黄河流域的中原河南,中国南北的分界线秦岭,以及嘉绒藏区、苏北水乡,六个作家,就是六片不同的土地,六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既然要表现中国的作家,第一要素就是他的地理文化。”

“其次,还要考虑到民族,所以我们选了一个藏族作者阿来,阿来是嘉绒藏族,但是他用汉语写作,这非常有特点。
第三,需要考虑性别,一定要有女作家,迟子建在我们的盛情邀约之下加入了进来。”

如何把这些作家与他的作品以及故乡结合起来?
“这就需要我们围绕作家的文学风格去设计拍摄内容和方法,使作家、作品和故乡完美地融合起来。
比如迟子建,她的小说很多背景都发生在冬天,所以我们选择冬天去拍,这个季节才能比较好的把她的作品给表达出来。其实我们也拍了一些夏天的景象,但是没有往里放,我觉得在风格上破坏了一致性。”

“再比如贾平凹,拍他就一定要展示秦岭,因为他这一生写的其实都是秦岭。另外,他的小说都是用真实的人物来做原型,我们这次跟随贾平凹回到故乡,还拍到了他作品中的两个原型人物,让我们更深层次地走进了他的作品。”

“特别有戏剧性的就是刘高兴,他原名叫刘书征,和贾平凹是小学、中学同学,中学毕业以后,因为家庭成分好去当了兵,贾平凹体检没合格,没当成兵,去修水库,再后来去上了大学,两个人的命运至此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后来贾平凹以刘书征为原型写了《高兴》,刘书征索性改名儿叫刘高兴,还写了本纪实小说《我和平凹》,把自己也变成一个旅游景点。”

“在贾平凹的生活里,他的人和艺术是如此的水乳交融,不可分割,他从生活中提炼出很多艺术形象,再进行艺术概括和加工,把生活和艺术完美地协调起来,这不仅为我们的纪录片拍摄提供了非常好的物质形象,同时也是进入贾平凹文学的一扇门,假如不是拍故乡,你很难用这种方式去走近一个作家。”
纪录片的首要表达方式是纪实,但在本片中也有非常多有“看点”的艺术化处理,是如何考量的?
“一个作家仅仅用纪实去表达是远远不够的,纪实很重要,没有纪实就没有动人的细节。比如贾平凹回到商洛要吃一碗糊汤,在一个小地摊,餐具简陋,还要站着等座位,但是他还是要吃,他要吃的就是他童年幸福的回忆,这是纪实手法带给观众的真实细节。”

“但是在表现苏北水乡作家毕飞宇的时候,我们尝试着在纪实之外,用了一些艺术化的表达方式。他说,‘水不仅在河里,水也在身体里’,所以我们想了一个表达方式,让他所有的转场都是在水上进行。
毕飞宇会划船,但几十年没划过了,找一个人划船,他坐在船上,也可以表达这种意境,但是,视觉上不纯粹,我们就给毕飞宇找了一根竹竿练习,最终他自己划船呈现出了比较唯美的画面效果。”

“另外,我们用了两个1分40秒的长镜头,一个是设计的,另一个是真实记录,艺术表达和纪实手段均发挥了它们的优势。
设计的那个长镜头,需要毕飞宇回到扬州大学,从外面穿进楼道,与年轻学生相遇,意喻看到自己的年轻时代,镜头调度复杂,毕飞宇前后走了7遍才拍成功,这确实不是常规意义上的纪录片拍摄手段,但是这个长镜头把作家的成长和内心变化更为直观地表现了出来。”

“另一个长镜头是在毕飞宇去寻找出生的地方时自然而然发生的,由于他30多年没回去过,找不着路,经过指点,找到了一个河湾,突然一扭头,他看到了当年生活的那个杨家小学,‘啊’的一声,他非常激动,我们的摄影师就一直在他身后静静地拍,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在他转过头来的时候,发现他是看见了他上小学的地方,这条长镜头如实地展现了作家的情感世界。”
拍摄莫言对中国文学具有重要意义,是如何构思表达的?
“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我触动非常大,他让中国文学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他已经成为当代伟大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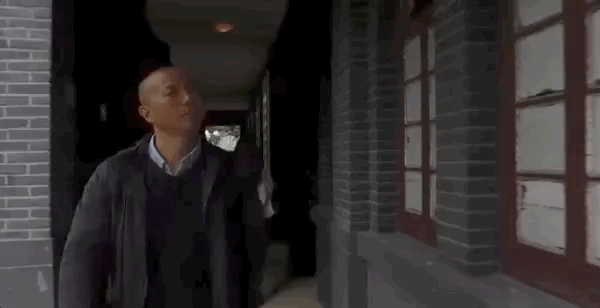
“拍摄前后跨越了3年时间,首先,还是要跟随莫言回到‘文学现场’,回到高密东北乡,脚踩着孙家口桥,讲述《红高粱》的浓烈传奇等。”
“其次,根据莫言的文学特点,用民间艺术的方式做点表达。我们大量使用了山东高密的民间艺术,我们找了当地一个民间艺人,用山东快书、西河大鼓、茂腔来演奏莫言老师的打油诗。假如这段说的是莫言当兵的事,就先由民间艺人把相关的打油诗演唱出来,然后莫言老师再出来。”

“我把老艺人放在什么地方?老艺人本来都是在舞台上演出,哪怕是搭着草台,但在我的拍摄中,我把他放到庄稼地里。在《红高粱》中写的小石桥上讲《红高粱》,在胶河滞洪闸,讲《透明的红萝卜》。我们拍了七首打油诗,这就是用民间艺术的方式来讲述莫言的故事。我还特别在里面讲了茂腔,莫言老师听得特别过瘾,这是他小时候经常听的。”

“用山东的民间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来装点莫言的文学,在内容上和精神气质上有一种内在的和谐,同时,又能够从纪录片的角度,找到了一种艺术表达的方式。莫言的小说文学具有非常强烈的现代意识,同时又有非常突出的民间特征,用电视去表达,不能是简单地跟踪纪实。”
拍摄本片最大的体悟是什么?
“关于文学的纪录片,只有文学,是拍不成纪录片的。文学纪录片的核心是怎么用纪实的方式,不仅拍出文学背后的故事,还要拍出文学的意境,这个其实是创作中最大的难题。我们也不能说这次做的就很成功,某一集好一点,某一集可能就稍微弱一点。”

“但是我们在努力探索怎么用电视纪录片这样一种以纪实为主的方式找到通向文学的一条道路,拍文学的故乡,可能是借助“故乡”这样一个梯子,进入到文学。那我也在想,有的作家他不写故乡,有一些作家,更多的是精神世界的探索,你怎么去表达?还有的,比如说是,里边没有明确的地点、人物、事件,你怎么去表达?”

“用纪录片去表达文学,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我希望不仅是我啊,也包括其他的纪录片制作人一起去努力寻找到用纪录片进入文学的方式。因为文学虽然不再是这个时代最普及的艺术形式,但是文学在人类生活中,我相信它永远不会衰竭,它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精神营养美学的花园。”
(罗石曼采访整理)
主编 | 杨 珺
责编 | 杨 畅